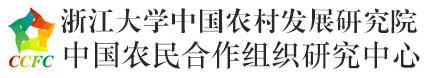“萝卜白菜议事规则”———南塘兴农合作社的“洋为中用”
站在一堆农村的大爷大妈中间,一个面色红润的青年格外显眼。他是这群人当中最年轻的,却是他们的头儿。
“开会了!”他一边说,一边拍手,然后右手握拳,举过头顶,嘴里喊着“五、四、三、二、一”,每喊一下,就把拳头挥动一下。刚开始的时候只有他自己喊,接下来就有人随着,喊到“一”的时候会议室里差不多就没人说话了。“好,再来一遍!”
这奇怪的一幕,不久前出现在一本书的最开头。书名叫《可操作的民主》。
没一个“说话算”的人
亲手创建合作社、担任理事长至今,又主持大部分会议的杨云标自己说话也不算
开头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小小的农村合作社里。
乍一看,这儿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村落,连位于南方还是北方都很难分清。一样见不到几个年轻人,一样凋敝的乡村商店,一样一桌桌喷着土烟打麻将的老人,土狗们摇着尾巴在他们脚边转来转去。路边立着一块大影壁,“阜阳兴农合作社简介”。
一栋三层的水泥小楼立在对面,这就是合作社了,全名是“南塘兴农合作社”,2007年领到的许可证。在中国的52万个农业经济合作社之中,它占一根手指的分量。
它有三种主要的经营活动:小额资金互助,现已有固定资本80万元;酿酒,每年大约可产销5吨纯粮食酿造的白酒;农用物资购销服务,今年的目标是销售300吨化肥。拥有2000名社员,和一个“理事会”,一个“监事会”。合作社的三层小楼是公产,2008年向社员内部集资盖成,价值20多万元。
从数字上一样看不出什么。你只有走到他们中间,在那张椭圆形会议桌前找到一把椅子坐下,才能发现一个诡秘的现象:在这个复杂的经济实体里,找不到一个“说话算”的人。
首先,这里的客人说话不算。
29岁的贵州人徐昌强吃了一个下马威。他原是一个肉鸡养殖户,此次被贵州一个支农NGO派到南塘合作社学习一个月。前几天,南塘合作社决定开一次会议,讨论如何激励老年社员在合作社开展绿色鸡蛋生产,轮到列席的徐昌强发言。他没多想,直接谈起养鸡需要的技术指标:这个鸡呢,首先要注意的是防病……
“小徐,一事一议。这个问题我们下次再议。”刚说两句话就被合作社的理事长杨云标——那个近乎谢顶的青年打断。大部分会议都由他做主持人。
其次,这里资历最老的人说话也不算。
82岁的退休银行职员唐金铎是合作社年龄最大的理事,照片就挂在资金互助小组办公室的最上方,标明“业务总指导”。“每个人都得有发言的机会,最后投票,少数服从多数。”这位老人还不时吐出一两个与他的年龄很不搭调的奇特名词:“动议”“议题”“表决”……
最有钱的人说话也不算。合作社最大的股东是78岁的退休中学校长时永林。在资金互助小组80万元的固定股本中,他一个人占10万元。合作社封给他最大的一个头衔——“参议长”。这个词的意思是:有些特别重要的事情,需要理事会和监事会同时参加,这两个会合称“参议会”。
如此雄厚的股本和荣耀的头衔,并没带给时额外的特权。他依然能一字一顿地讲出合作社开会的两条规矩:一人只有一票;轮流发言,不得抢答。
原先说话算的人,到这里也要改改自己的脾气。矮胖子唐治和在加入合作社前是个成功的肉商,“跟我合作的生意伙伴都必须听我的”,他一抿嘴,显出对自己权威的自信。“别看我就念过三年书。”
如此自信的唐治和,很快就领教了这里开会的规矩:主持人杨云标经常会打断他:“老唐,今天每人只有两分钟发言时间,你省着点”:“老唐,别抢,现在轮到人家说”:“老唐,别吼,有什么话对着我说”:“老唐,”……
亲手创建合作社、担任理事长至今,又主持大部分会议的杨云标自己说话也不算。“主持人也只有一票”。他笑眯眯地说。“大伙儿说了才算。”
一言堂还是一盘沙?
一位老人说,“还不如咱原先大队开会。那时候都听队长一个人的,吵也吵不起来”
从前,会并不是这样开的。
2001年,时年28岁的杨云标在他的家乡——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三合镇南塘村,成立了“农民维权协会”,它就是今日南塘兴农合作社的前身。
安徽作为中国农业大省的历史已有上千年。这里不仅诞生过小岗村,也产生过一部《中国农民调查》。这部由合肥市作协主席陈桂棣夫妇合写的纪实文学,诸多内容正来自阜阳市,描写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苦难到骇人听闻的农民生活。
从1998年大学毕业回家起,土生土长的杨云标不可避免地成为附近农民上门求助的对象。问题无非几大类:不堪重负的提留款,不透明的村庄账目,贪污腐败的村干部。他曾有统计:一天最多接待过34拨求助者。
杨云标成了这一带农民维权上访的骨干人物,政府眼中的“刺儿头”。他曾与一位名叫唐殿林的村民卖掉自家的猪做路费,还惊动过常务副省长亲自批示。“那些年撤掉的村官,十个二十个总有吧”,他带点笑意。
当维权上访不再成为乡村生活的主要内容,“农民维权协会”进化为南塘兴农合作社。在经济方面,农民们团结的力量同样毋庸置疑。通过合作社,他们可以买到既便宜又质量上乘的化肥。从前,一个农民一年只能买几袋化肥,即使发现失效,索赔的能力和成本,都是个人所不具备的。有了组织之后,为了揽这个一次可买几十吨化肥的大客户,经销商们一趟趟地往村里跑,维权也有坚固的保障。
然而,这只是相对的团结。对外界而言,他们是一个整体;对内,农民们恰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说,像一个个土豆般,各行其是。
从“开会”这种最日常的集体活动上,杨云标就感觉到了团结之难。
有人跑题,东拉西扯;有人相互攻击,不断地从主张的不同扯到陈年恩怨;有人为自己的利益坚持主张,而又不懂得让步;谁说话声大,谁就往往占据话语主动权,可以影响众人;谁生性内向,谁的利益就往往被忽视,而在暗地里心怀不满……
合作社几位理事回忆:2007年左右,合作社矛盾冲突不断,不断有人在会议上争吵,吵着吵着一拍桌子,拂袖而去,搞得人心四散。矛盾最激烈时,杨云标曾气得差一点解散合作社。“还不如咱原先大队(村支部)开会。那时候都听队长一个人的,吵也吵不起来。”一位老人说。
杨云标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感到了中国农村政治传统的可怕魔力。不断有人受不了这种一盘散沙的乱象,当面对他嚷:“就是因为你杨云标不敢干,才搞成这样。你要是当头,我们都跟着你……”
这种状态,与合作社刚成立时,他参加的一次会议上讨论的结果巧合。那次讨论的问题是:农村最缺什么?人们大部分赞成的一个结论令他心里很不是滋味:“缺好的领导”。
但杨云标拒绝“当头”。多年的带头维权经历,带给他更大的担心,“总是一个人说话算下去,集体对这个人就会形成依赖,崇拜;这个人本身也会开始膨胀,自我和独裁,排除异己。”他分析。“谁都一样。”
在这种气氛中,他日益感到合作社的整体氛围“越来越像一个官僚机构”,决定越来越像命令,层层下达,推动也越来越依赖自上而下的个人权威。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推着他向两个方向走:要么一盘散沙,要么一言堂。这只手看不见摸不着,却力大无比。
“萝卜白菜,开会顺利”
《罗伯特议事规则》漂洋过海到南塘,完成了本土化
转折出现在2008年5月的北京。通过女作家寇延丁和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负责人刘湘波,杨云标认识了从美国回来的袁天鹏。
1976年出生的辽宁人袁天鹏也遭遇过杨云标类似的问题,在他读本科的北京邮电大学。
中国的大学生们在开会这个方面,跟养育他们的农民没有多大区别。在北邮,袁天鹏这个学生会主席经常想“民主一把”,不擅自决定而让大家讨论。结果,会议往往开成一次马拉松,两方面意见相左,议而不决。他越来越深地领悟到:鲁迅说中国人“没有皇帝,日子怎么过”,绝非奴性,而是一个基于现实的核心问题。
而在他读硕士的阿拉斯加大学,袁天鹏发现了一种全新的,对会议弊病的解决之道。他申请做了学生议会里的“议员”,议会秘书给他一本书,《Robert‘s Rules of Order》,示意他:从这里面学开会。袁天鹏吃惊了:《罗伯特议事规则》?(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十年之后,他成为这本书第十版的中文翻译者。
根据这本书的自述,亨利·罗伯特准将,是生活在美国19-20世纪的一位工程兵将领,在民间组织和教会中从事多年会议实践,他也深感会议的低效和争吵,将精力倾注于开会的诀窍。1876年,他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便是这本《罗伯特议事规则》。其中,一些最重要的经验来自于英国议会下院的议事法规。一百多年后,袁天鹏放弃了自己原先所学的电子工程专业,决心将推广这本书及它的内容,作为自己的第一事业。
经过香港乐施会出资,2008年10月-2009年2月,袁天鹏来到杨云标的合作社,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罗伯特议事规则》培训。
历经百年的不断补充、修改、注释,《罗伯特议事规则》从一本首版一万字的小册子,变成了一部七百多页、光前言就接近两万字的大部头。漂洋过海到南塘,它完成了自己的本土化。
为了让三十几个平均年龄接近七十岁的农民理解它,袁天鹏绞尽脑汁,让他们一步步明白种种道理:“哦,原来美国人从前开会也打架”:“能够做主持人,不是因为这个人英明伟大,而是在他背后有一个制度,有一套如何开会的规则,不仅明确了主持人可以有怎样的权力,也明确了主持人不能做什么”……
经过几个月的培训、听讲、发言、争吵、解答,这部七百多页的书名字已经不叫“罗伯特”,农民们顺嘴把它变成了“萝卜白菜规则”,变成一首1分48秒的歌。
67岁的老太太王秀华当年是跟杨云标一起维权的农民运动骨干,而今是合作社的文艺队长。她编了这首《萝卜白菜议事歌》:
“有口难言,主持中立;要算本事,得算是动议;举手发言,一事一议;面向主持,免得生气;限时限次,公平合理;立马打断,不许跑题;主持叫停,得要服气;正反轮流,皆大的欢喜;首先表态,再说道理;依事论事,不许攻击;话都说完,再说决议;先正后反,弃权就没戏;多数通过,平局没过;萝卜白菜,开会顺利;萝卜白菜,开会顺利!”
这首歌,至今三年了。
和稀泥?
“其实哪儿又有‘最好’这一说呢?”
三年后的今天,中国农村一贯秉持的能人治村原则,正在被来自大洋彼岸的“萝卜白菜规则”悄然无声地化解。
跑题、野蛮争论……如今,南塘合作社的会议室里已基本见不到这些弊病。同时,“一盘散沙”,决议效率低下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不再可能出现一个强者的一言堂。只是,会议商讨出的结果,往往与一开始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都不一样,总是取一个中间值。
酒厂目前有十几万元的股本总额。最大的股东,就是身为厂长的唐治和。然而,对酒厂而言,至今最剧烈的一次命运转折机会,他的意见照样被否决。
第一批酒酿出来,迅即发生了争论:卖纯粮食酿造的白酒,还是勾兑?后者利润比前者要超出几倍,诱惑很大。唐治和私下里把勾兑用的酒精原料都买来了,认为跟大家打个招呼即可直接通过。
没料到的是,经过逐次发言讨论和投票表决,他的想法被毙。合作社一名参与那次会议的理事摇着头说,自己和杨云标一样投的是反对票。“我俩都觉着,勾兑早晚得把牌子砸了”。
几乎每件事情的讨论,结果都是一个博弈的过程。一个月前,合作社召开参议会,讨论今年化肥的销售价格,一袋是卖115元,还是120元?虽然只差5元,但在这个皖西北农村,已经是农民在种田时不能忽略的重要成本差。
时永林主张卖115元一袋。合作社用来做化肥生意的资金都是从资金互助组的贷款,要还利息;他想以价格优势尽快卖掉。但另外一种意见寸步不让。“后来社里投票。(购买者)要是给现钱,就115;要是等收完麦再给,就120一袋。”
在讲述时,这位老人并未露出不满的表情。“这样挺好,意见都照顾到。”
酒厂的一次争吵也是如此。合作社面临着两种选择:约占三分之二的人想把酒配上价值近10块钱的包装,一斤一瓶卖50元;这样,村民们婚丧嫁娶时,看着档次高一些,可以提高销量。
另一部分股东兼消费者则不主张这么做。他们多是上年纪的老人,只想降低自己的生活成本。他们要求直接卖散装酒,26元一斤。他们的理由也很充分:咱这酒连许可证都没有,就是个小打小闹,卖自己乡亲喝的,要那么多包装干啥?
最后,合作社还是通过举手表决,决定了最后的销售原则:一部分酒打上包装,卖给想要待客的家庭;另一部分酒则散着卖,专卖那些想要自己喝的老人。两种酒的数量之比,正好跟这次争论的两派人数大致相等:2:1.
这与《罗伯特议事规则》的核心原则一致:“谨慎仔细地平衡组织和会议当中人或者人群的权利”。
“这不成了和稀泥吗?”
对南都记者的这个问题,袁天鹏的解释是:民主做不到‘最好’——效率最高;它只能起到一个协调的作用。
他稍稍停顿一下,露出一个曾去美国留学的中国人常见的困惑表情。“其实,哪儿又有‘最好’这一说呢?想要‘最好’,一蹴而就,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杨云标已感觉到,几年前那股越来越重的官僚气息,减轻了很多。
如今的合作社开会,人人都习惯“晚一步”,彬彬有礼地先让其他人发言,再也不是从前那种“先下手为强”“谁嗓门大谁就有理”的状态了。他理解:民主的本质是博弈,如同辩论。既然要辩论,先知道对方的论点,肯定会更有利一些。
一直被传说,从未被复制
一位最有可能扩散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基层村官,却没有丝毫作为,他说“跟组织原则有冲突”
虽然2007年,南塘村随着行政区划改变而与另外两个村子合并成“三星村”,但南塘合作社的名字沿用至今。罗伯特议事规则的知名度亦在不断攀升,连古稀老农都能绘声绘色地讲出几个关于“萝卜白菜规则”的传说。
合作社采用集体决策的效果,正在慢慢出现。去年,它引入了附近十几名商人的资本,股本总额达到了近300万元。三年来,它没有出现过任何数得上的政策失误。甚至有人说:如果早一点学会开会,2008年那次险些导致合作社解散的危机完全可以避免。
它的使用者更是大受影响。唐治和经常跟儿媳妇讲:“有些事,不要硬头皮去做,还得靠大家定主意。”尽管他仍会私下里谈到合作社为酒厂定的某个决策,觉得自己的战略眼光比大多数人高明却不被理解。“我保留意见”。
饶有意味的是,本土化的罗伯特议事规则却几乎从未在合作社外发生过复制和扩散效应。首先表现在党支部、村委会这些似乎最可能受影响的基层政权组织。
当年那位卖掉自家的猪做路费,与杨云标一起进京上访的唐殿林,如今已是三星村的村支部副书记、兼村委会副主任。这么多年,他与杨云标的交情仍十分坚固,担任着合作社资金互助会的副监事长。
这样一位双重党政角色人缘极好,在不久前的镇人大代表选举中,全选区1159张票,他凭1069票以第一名当选,因为找他办事帮忙的农民太多,他的手机号码在乡间被称为“南塘110”。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最有可能扩散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基层村官,却没有丝毫作为。究其原因,他很简洁地给出了解释:“跟组织原则有冲突”。另外,“也不是大伙都同意的事儿就对,有时候还得听领导的”。
唐殿林很不满意地举出一个例子:当初正是他想出了让合作社批量购买化肥卖给村民的点子,但他是主张不加价、不盈利的。结果合作社大多数人否决了他的主张,将此举变成了一种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商业行为。合作社变成了一个经销商,而且是一个价格并不具备多少竞争力的经销商。“现在我那个村,买合作社化肥的,十家里头没有一家。”
袁天鹏个人的经历,似乎更能为“跟组织原则有冲突”提供一个注脚。成立专门公司推广罗伯特议事规则、自任总经理5年了,一直孜孜不倦地推广罗伯特议事规则的他,至今仍是公司唯一的一名员工,主要收入是演讲。“最难推广的是政府”,他在接受一次媒体访谈时脱口而出。
“这套规则是议事规则。”袁天鹏补上一点:切忌处处都用它,什么都要表决,那就成了“泛民主”。“美国国会讨论用它,但美国总统跟下属下命令的时候,是不能用的。要是处处都用,那根本没法干事。”
国内各类NGO是罗伯特议事规则的主要客户。如寇延丁,就一直在她的NGO中使用并推广。
“从古到今都存在议事规则,不过传递的价值取向不同。”壹基金秘书长杨鹏说。
杨鹏长期担任过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秘书长,这个素有名气的NGO如今遵循的,也正是这套罗伯特议事规则。在他看来,王石、冯仑这些企业精英和南塘村的农民遇到的问题,大同小异。不久前,北京召开了一个研讨会,研讨寇延丁和袁天鹏合写的那本书,《可操作的民主》。
“大家说完了,皇上说了算,所谓‘从谏如流’嘛。”在会上,杨鹏揶揄,中国从古到今,遵循的其实都是“民主集中制”。
唯一的一点扩散迹象,出现在资金互助会的监事长,三合镇三合村的村委会主任唐殿成身上。
这也是一位与杨云标关系甚笃的村官,以敢于顶撞不合理的行政命令出名,同时也是一个经营农用机械的商人。他刚申请成立了一个合作社,准备结集几个有实力的农机商,搞一个经济实体。他想请杨云标来讲课,讲讲怎么开会。(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我们懂怎么做事,但不懂怎么合作,怎么把事做大”,经常来南塘合作社旁听会议的唐殿成说,此举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谁拿钱多谁就说了算”。(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在展望效果方面,唐也出现了些许犹疑。他总结:用罗伯特议事规则讨论,可以保证最后得出的结果符合大多数人的主张,不会出现某个领导者脑子一热、集体损失惨重的闪失。但是,这样无法“实现跨越式发展”,速度和效率上不去。南塘合作社发展了这么多年,还没有吸引到几个年轻人加入,便是证据。
两块无力的塑胶板
目前合作社急需进行议事规则第二季培训,给合作社制订一部“宪法”
学会了开会,现实仍然需要一点一滴地改变。
尽管合作社已有来自阜阳市三个县区的2000余名社员,被全国媒体这么多年来当做“新乡村建设”的典型一再报道,但这个数字其实只占到三星村本身6000余人口的三分之一;对阜阳这样一个人口过千万的超大城市而言,更是九牛一毛。除了在外打工的青壮年无暇参与外,不少人都对南塘合作社抱有看法:他们曾经是一个整天上访、抗议,反映官员贪污腐败的组织,说不定哪天就干不下去了。
这靠罗伯特议事规则是无法奏效的。要想打动他们,只有当合作社发展强大到让他们心动,觉得再不加入就要承受经济损失的程度。
但即使在合作社内部,它产生的利益也不足以把每个人维系起来。从2004年成立至今,合作社从来没有给它的运营者们发过工资。从理事长杨云标到合作社整体,都没有任何的经济奖惩手段。无论酒厂厂长还是资金互助小组的业务总指导,都是“良心工”——白干。
他们所得的,不过是跟每一个加入合作社的普通农民一样,按照股本分红。诸如,去年每入股酒厂1000元,可以分一箱价值100多元的酒。作为理事长的杨云标至今还跟父母住在老房子里,墙壁上的大裂缝触目惊心。唐殿成就对合作社的发展速度很不以为然。“我的合作社干起来,三个月,实力就能超过他们。”
至于用岗位的升迁作为管理手段,合作社就更没有了。成立至今,从未有成员因为工作表现而被升职或是降级,谁干哪个职位,都是毛遂自荐,各显其能。合作社唯一可称为奖惩手段的,是办公楼一楼会议室里挂着的两块塑胶板,一块写着“光荣榜”,一块写着“加油站”,分别写上工作优秀或是欠佳的人员名字。恍然幼儿园贴的小红花。
随着合作社一天天变大,可能担负的责任越来越重。一些不祥的征兆已经出现:资金互助组的出纳以健康为由辞去了职务,要求去做了酒厂的会计:“我推测,他是怕出事担责任”,杨云标无奈:合作社至今还在用圆珠笔记载每一笔存入和借出。
他还发现,下属的各个团体,总是把事务推到合作社层面,要召开大会,集体定出一个结果。越来越有袁天鹏所说,“泛民主”的意味。“……合作社是领导我们这个部门的,我们当然得听合作社的嘛。”面对南都记者,一位67岁老人为自己辩解。
这些做法都令杨云标充满躁动,但他确实很无力,除了那两块塑胶板。这已经不是“奉献”与否的问题,而成为阻碍合作社下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他坦言:目前合作社最急需的,是进行《罗伯特议事规则》的第二季培训,给合作社制订一部“宪法”,规定哪些问题应该用罗伯特议事规则讨论,哪些则不需要,直接执行即可。这就势必要求制订好从上到下,每个层面的责任、义务及权利。届时,势必要引进物质利益作为奖惩手段。
换句话说,矛盾与争吵的激烈程度将要远超如今。
有口难言,主持中立;要算本事,得算是动议;举手发言,一事一议;面向主持,免得生气;限时限次,公平合理;立马打断,不许跑题;主持叫停,得要服气;正反轮流,皆大的欢喜;首先表态,再说道理;依事论事,不许攻击;话都说完,再说决议;先正后反,弃权就没戏;多数通过,平局没过;萝卜白菜,开会顺利;萝卜白菜,开会顺利!
———《萝卜白菜议事歌》
-
“中国农村改革40年:农民合作社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暨第六届“中国合作经济中青年学者工作坊”在杭州顺利召开08-23
-
中心主任徐旭初教授带队赴山东调研07-27
-
值得推荐阅读的农民合作社研究论著(2007-2016)07-23
-
2017年值得推荐阅读的农民合作社研究论著07-23
-
“中国农村改革40年:农民合作社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暨第六届“中国合作经济中青年学者工作坊”会议通知【更新】04-03
-
中国农民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徐旭初教授带队赴晋调研08-06
-
第五届“中国合作社经济中青年学者工作坊”在山东泰安顺利召开07-27
-
第五届“中国合作经济中青年学者工作坊”会议通知07-08
-
中心主办“合作社法律修订专题研讨会”在陕西顺利召开11-30
-
中心主办“合作社法律修订专题研讨会”在陕西顺利召开11-30
-
2015年最值得推荐阅读的中国农民合作社研究论著07-27
-
徐旭初教授为苏州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辅导员培训班授课07-08
-
黄祖辉教授等撰写的决策报告获中央领导重要批示07-02
-
黄祖辉教授做客宿州大讲堂 阐述创新型农业现代化先行区发展路径06-20
-
浙江大学中国农民合作组织研究中心(CCFC)设立浙江分中心06-20
-
农民专业合作社申办流程及相关材料08-05
-
徐旭初:烟农专业合作社发展的若干问题02-01
-
马文杰:农民合作社解析12-09
-
沈卫彬:农业合作社生产标准控制与质量分级12-17
-
国际合作社联盟:“合作社十年(2011-2020)蓝图”计划草案[英文]11-05
-
美国农业部:合作社是什么?以及成员、理事、经理和雇员的角色10-12
-
Baqui Khalily: Capacity Building for Cooperatives08-22
-
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写参考大纲08-09
-
王景新:中国乡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趋势、问题与政策07-28
-
范金旺: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管理07-20
-
Gall & Schroder: Agricultural Producer Cooperatives as Strategic Alliances07-12
-
霍学喜:农民专业合作社功能及服务模式06-22
-
农业部:首批6663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联系方式06-12
-
王征兵: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思路与对策06-03